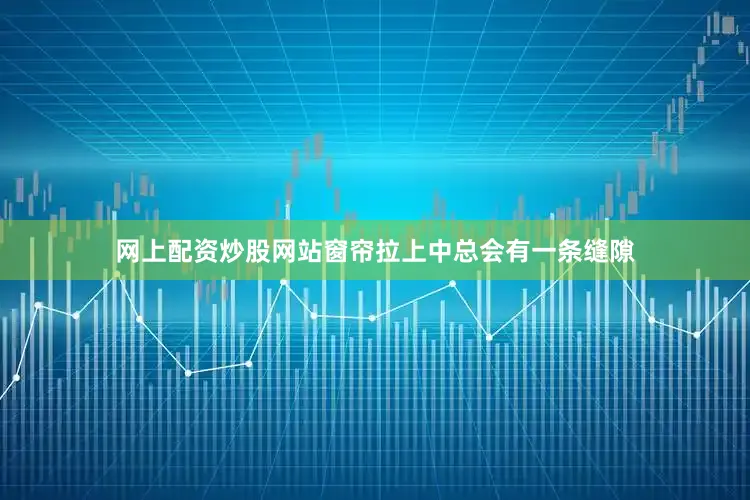艺坛对话
中西美学的交流与超越
——关于高建平专著《中国书画中
看不见的身体》的访谈
采访人:安静
高建平先生的著作《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The Invisible Body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出版。该著作是高建平先生于199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7月曾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原名是《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 From Calligraphy to Painting)。采访人拜读了这部作品,并对其中的多个话题产生了兴趣和思考。此次专题采访,高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生涯与该书写作入手,畅谈了中西美学沟通的重要性,并结合学术研究现状抒发了自身对现代美学发展前景的思考,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一书的认识,而且为“三大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展开剩余95%△ 《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 高建平著,张冰译
一、学术历程与著作的诞生:从“画境探幽”到“看不见的身体”
Q
安静:高老师,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以绘画美学入手来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这部学位论文的出版情况,以及这次中文书名调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高建平:这本《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是我当时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读书的时候写的。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画境探幽——中国绘画美学初探》,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画境探幽——中国绘画美学初探》由一组学术论文构成,其中有一篇是谈论中国书画的书写性原则。《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中的主要思想来源于这篇文章。我研究绘画美学的出发点是读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特别是其中的几篇文章《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以及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以这两本书为基础,但又与这两本书有很大的区别。在关于中国画的理论方面,我受这两本书的启发,阅读了俞剑华编著的《中国画论类编》和黄宾虹、邓实选编的《美术丛书》;而在美学理论上,则是读了恩斯特•贡布里希(E. H. Gombrich)的《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的《视觉与绘画》(Vision and Painting)等一些书,当然,其中一些关于眼与手关系的观点,也可看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一些人的观点的影子。在做法上,我是从中国画论的原文出发,将理论从这些中国古人的论述中抽引出来,而不是将一些哲学和美学理论加到古人的论述之上。
也许,这是第一本直接用英文写的中国美学理论著作。在我的这本书出版之前,有一本英文的中国美学著作,由朱立元先生和吉恩•布洛克(Gene Blocker)合作,选了一些重要的中国美学论文译成英文出版,在英语的美学界有一定影响。另外,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在那时也译成了英文。直接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美学著作,这应该是第一本,最早在1996年出版。
这本书最初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Almqvist & Wiksell国际出版社出版,当时印量不大,但通过交流,在世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有收藏。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不少书评。在这些书评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篇。
第一篇是美国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书评。阿恩海姆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学家,他所创立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艺术与视知觉》(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曾由滕守尧先生译成中文。滕先生曾回忆,1980年,第一届中华美学学会大会在云南召开,他作了关于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的发言,受到朱光潜先生的高度赞赏。后来阿恩海姆的其他几本书也陆续被译成了中文。我的这本书出版时,阿恩海姆还健在,当时已经九十多岁。我给他寄了一本,他回信说,谢谢我给他寄书,也许会写一篇书评。后来他果然写了,并且发表在《英国美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上。阿恩海姆的这篇书评对我这本书中的观点有赞同也有反对,而这恰恰反映了我和他思想的不同点。阿恩海姆所主张的格式塔心理学派,最终还是从康德哲学发展而来,主张精神与物质既二元对立又异质同构。对康德的二元思想,我在书中是有质疑的,我所主张的是精神与物质统一于人的活动,由此形成“活动—动作—实践”一元论。
第二篇是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毕莱德教授撰写的书评。毕莱德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的书评是用法文写的,共有十页,发表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家汉学杂志《艺术通报》(Art Bulletin)上。在欧洲,荷兰的汉学历史悠久,荷兰的莱顿大学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汉学专业,而这份杂志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篇书评主要在细节上进行论述,展现了这位教授关于中国艺术的丰富知识。
除此之外,很多西方美学家们都提到过这本书,例如阿列西•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海茵茨•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等学者都在各种会议上对这本书作出评论,表示很喜欢这本书所具有的“理论的彻底性”。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这本书。美国美学家、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柯蒂斯•L.卡特(Curtis L. Carter)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也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引用了这本书。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国际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引用。哈佛大学的苏珊•布什(Susan Bush,中文名卜寿珊)教授在为《牛津美学百科全书》写“中国艺术理论”辞条时,将这本书列为关于“中国艺术理论”的十部参考书籍之一。
这本书的书名在初版时是《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这次出版调整为《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这是应出版社的要求所作的一次调整。出版社认为,“表现性动作”一词有一点抽象,学术味重,建议换一换。我就想到了“看不见的身体”。其实,这是此书原来的书名。当年论文完成提交后,我在瑞典的导师约然•索尔本(Göran Sörbom)在理论上比较保守,对body一词敏感,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我改成了expressive act。当然,“invisible body”这个词也不是我的发明。这个词源于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的《视觉与绘画》(Vision and Painting)一书。这本书中说到,看到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的董源和巨然的画,我们无须见到画家作画动作本身,在画中就可看到画家的“看不见的身体”。这次中文再版,是原名的恢复。
二、线•时间•身体:中西画论的交流与碰撞
Q
安静:您刚才的讲述向我们揭示了这部书背后的学术史以及您思想发展的脉络。您在书中以“意、气、势、笔”来统摄中国绘画的新美学,整个布局从对“线”的讨论开始,丝丝入扣。一开始读来并不觉得理论艰深晦涩,反倒像不经意间的信手拈来,但整体逐渐成“势”。回过头再体会您的行文之“气”是如此贯通而磅礴,最终落“笔”,结论让人心悦诚服。既然“意在笔先”,您讲书画同源,是从“书”入手、从“线”开始进行研究的,这个切口是怎么找到的?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线”的艺术,或者说“线”在中国艺术中的独特性是什么?
高建平:我当时是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读美学,当然读的书都是关于西方美学的。此前我在中国是读完中文系的本科、美学专业的硕士,然后才到瑞典接着读博士。由于当时中国与欧洲在美学上的教学体系不一样,知识结构也不一样,欧洲大学美学专业的学生在硕士期间读的书,甚至本科读的书我都没读过。我所在的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在不同层次上办学。我入学后,有些知识要从本科补起。比起美国,瑞典的教学制度富有弹性。从形式上讲,我是直接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对我原有的硕士学位也是承认的,但是,系里的其他同学读过的书,我还是得补读。在那里的几年,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读美学系的学生一般都要读的作为基础知识的书,同时也要跟上学术的发展,读一些当时在学术界流行的重要著作。当然,我在去瑞典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美学的研究基础,也曾写过一些中国美学方面的文章。于是,在那些年所做的事,就是读西方美学的书,在对比中思考中国美学的特点。
西方美学有一个大传统,那就是形式主义传统,从数学的角度理解音乐,从几何学的角度理解造型艺术。这个传统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开始,他们将图像几何化,是为了从世界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寻找他们认为更本质的东西,从而形成构图的规则,这与他们在偶然的世界中寻找必然的规律、在感性的世界中寻找理性的规律是一致的。他们从图像中看到几何图形,认为这才是对象的美的本质研究。丢勒写过一本书,讲如何运用圆规和直尺来作画。与这种美学观相反,中国人反对几何化,反对用圆规直尺这样的绘图工具来作画。中国人认为,线之美就在于徒手画出的美。用了圆规直尺所画出的线,就没有了生气,以此画出的画就是“死画”。
为什么徒手画出来的就不是死画,用圆规和直尺画出来的就是死画?这种论断有着深刻的哲学上的道理。徒手作画的时候,作画人的心意状态、身与手的运动,是对已经画出的线与形的延续和应对,使画成为了动作性的整体,而用圆规直尺来作的画,这一切就都没有了。原本“画”是“去画”,从动作到图形,而一旦用了规尺,就成了制图,心意的表现、身手的运动,都化为了静态的图像。
中国的绘画受书法的影响,这句话宗白华先生就讲过,但绘画是如何受书法影响的,他没有详细展开。例如,我这本书从一根线的美谈起。什么叫一根“线”?几何学可以给它一个规定,那就是两点之间在平面上最短距离的线是直线,而中国人说“线”就是用手去画一根线。这根线也许没有尺子画出来的那么标准,但是手画出来的线包含着从“意”到“气”到“笔”再到“墨”的过程,包含着人的气韵风神,包含所有情感性、动作性的东西。这一层意义,就是中国书画的逻辑起点。
你提到“书画同源”说,对此我在书中做了专门的论证。“书画同源”本身只是一个命题、一种话语。它本质上不是在陈述书和画来自同源这样的事实,而实际上是说“画”在攀附“书”。我在这本书中说了这其中所蕴含的双重“攀附”:第一重“攀附”,是说“画”与“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画“与六籍同功”。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表现,“文明”就是以“文”而“明”。第二重“攀附”是书画同笔,即“画”向“书”学习用笔。书法用笔讲的是力量的轻重、方向和顺序,以及虚实和对称,而这些存在于书法中的感受可以运用到绘画之中。
Q
安静:当进入论文的展开部分之后,您重点抓住了“动作”这一核心关键词,分别从表演、表现、力量以及势、韵律还有时间来谈中国书画动作中所蕴含的艺术哲学原理。我注意到您对其中的“时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层,时间其实也涉及到次序、势以及韵律等相关问题,揭示了作画动作与时间的密切关系,并且时间也是一切哲学展开的基本维度之一。当读者或欣赏者与书法或绘画作品再次相遇时,对时间的感知构成欣赏的一个重要条件。您是否愿意就中国书画中的时间问题再多展开讨论一下?比如欣赏者感知的时间和作者时间的交流。中国书画的“时间”在当代绘画方式中还有多少保留,比如说动作化的时间在一些巨幅的画作中是否存在?您为什么没有专门谈中国书画的空间问题?虽然有涉及,比如说方向等。关于中国书画中的时间和空间,您还希望在访谈中与我们读者再交流哪些内容?
高建平:我想说这样几个意思:首先,为什么“书”对“画”很重要,这可以从心理建构上找根据。虽然书法在今天变成了一种专门的书法艺术家专有的才能,但其实在古代社会里,它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训练。人人都要练字,从小就开始,属于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在处理公务和私人交往中大家也都要写字,是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日常的写字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书法美的追求,形成了对线的审美意识。
这种审美意识,是书法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的心理桥梁。练过字的人,与没有练过字的人,看书法作品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练过字的人,用自己的书写动作来体会书法作品的用笔和结构。他们看到优秀的书法作品时,会忍不住用右手在左手上仿写,或者在地上、墙上、桌上用指头的动作感受书法家的动作,将作品看成是书法家动作的痕迹。
同样的心理桥梁也存在于画家与绘画欣赏者之间。对画欣赏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有对用笔动作的欣赏,也有对色彩、结构的欣赏,更有对所画内容的欣赏。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将“用笔”的因素扩展到极致,通过“用笔”来追求绘画的抽象,用线本身的美来超越“形似”。这种抽象的线条美,也要有所依托。它所依托的,正是这种对动作的感受。通过这种感受,沟通了“书”与“画”,也沟通了画家与欣赏者。这时,主客间的心理桥梁的作用便有了新的扩展。
“动作”这一桥梁的作用,还在于通过它,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内在情感与外在现象结合在了一起,实现了对审美上的二元论的克服。受康德美学的影响,一些20世纪的西方美学家用精神与现象间的“异质同构”的关系来解释艺术中的情感表现,从而造成精神与物质间的隔河对望,造成不同存在论层面上的“模仿”。“动作”就是通过人的活动,在精神与物质间架起一座桥梁。人的活动,既是精神性的活动,也是物质性的活动,人们边做动作,边有内心感受,并且外在的动作与内心的活动相互间密不可分。这种“动作”成为接通主客的出发点,是克服主客二元论的关键点,它应该成为现代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
我在书中说到了“表演”,是想澄清这样一种情况:书和画本质上不是表演艺术,但表演可凸显动作的重要性。书画是动作的痕迹,而不是动作本身。有一些书法家当众写字,一些画家作画一挥而就,在写字作画时有特别的动作,动作本身具有一种观赏性。但是,书法家和画家不能为表演而表演。这里存在着“表演”与“表现”的关系。书画家是在“表现”,而不是在“表演”。如果是在“表演”,落脚点就在动作本身,而“表现”是从动作的痕迹中看出。有一些书画家作书作画动作惊世骇俗,以此吸睛,那就走偏了。
关于“表现”,我想说的还是动作表现。这里的“表现”,与克罗齐对“表现”的理解不同。克罗齐讲“直觉”即“表现”,是一种心理的活动,与动作无关。我所说的“表现”,主要是想强调“表现”里面无论如何都少不了“动作”,通过“动作”来展现情感,成为形式,而不是情感的直接喷涌。实际上,我更愿意强调,没有什么抽象的情感,情感只不过是活动的伴随状态而已。
回到你的问题,即我在这本书中为什么主要谈时间,而很少谈空间。先说时间,关于绘画的时间,有多种理解:第一,绘画是表现的某一瞬间。如某个人在做什么,一组人在做什么,由此形成了一个个戏剧性场景。这种画不表现时间,只能如莱辛所说,通过对某一瞬间的再现来暗示时间。当然,在这些作品中,有些有意淡化其时间性,如一些神像和佛像,从中展示的是一种永恒性。还有一种是将不同时间的对象放在一起,例如拉斐尔的《雅典学园》。第二,通过绘画讲故事。例如绘画中讲圣经故事:从圣母受胎,到耶稣的诞生、成长、传道,以及受难过程,最后是复活。通过这些画讲述了耶稣的一生,也具有了故事的时间。类似的故事在佛教中也有。各种世俗绘画,或供儿童阅读观看的连环画,都是通过绘画来讲故事。
△拉斐尔《雅典学园》
除了以上两种对绘画时间性的理解以外,还有第三种,这就是绘画时间。这种绘画时间,并不简单等于画一幅画所需要的时间。在西方,画一幅画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三年或者五年,甚至更长。在中国也是如此,画家可能会反复酝酿,然后落笔。那只是绘画所用的时间。这里所讲的绘画时间,是绘画过程在作品中体现出的时间。这是一种表现性的时间。中国古代有一种“九朽一罢”的说法,是指画家可以精心打草稿,花很久的时间来勾勒很淡的一些线条。这些都是绘画时间开始前所用的时间。开始作画时,就要一气呵成,不能断,在绘画中体现出画家从“意”到“气”到“笔”再到“墨”的过程,在画中展现画家的气韵风神。
刚才你问的是“空间”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没有专门谈空间,但其实,也谈了空间,这就是空间的时间化。当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画面直接映入眼帘,是一个共时的空间。但是,中国人要求欣赏者把看一幅画化成“我看”和“我感受”的过程。
回到书法对绘画的影响。对书法作品的欣赏要回到书写的过程。我看一幅书法作品,并不是像看一幅照片一样,看一幅图形或一片风景,而是给我一个感觉的引导,让我在心里模仿作者将它写一遍。对中国绘画,也要这么理解,即要观赏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动作感觉的还原。绘画动作本身是有顺序的,观赏绘画也要实现顺序的还原,这就形成了空间的时间化。
把空间转化为时间,即转化为你对作品的接受时间,而接受时间又和作画时间构成“通感”的关系,变成“共情”的感受。这就是以我的感觉来感受对方的感觉,这是一种将心比心,而这一切其实和方向、顺序都有关系。表面上看,方向是个空间问题,但是把它转化为顺序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时间问题了。
Q
安静:读您的这部书让我时时想到宗白华“散步美学”的风格,您刚才也提到您写作的起点的确受到了宗先生很大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您的著作更加体系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论述对象,当然,这也与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着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您以书画为纲,兼论中国的音乐、舞蹈等其他门类艺术(甚至包括围棋),您用行云流水的文字,在比较视野中形成对中国艺术哲学的整体性思考。西方有“视觉是最高级的感觉”这样一个传统,而中国美学却以“气韵生动”为上。您从以视觉为主的书画,看到背后具有综合感官的“身体”,您如何评价在身体中的视觉的意义和地位?还有,宗先生作为现代美学开宗立派的学者,您认为您汲取了宗先生的哪些营养?您作为新一代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如何评价宗白华先生的美学,以及您认为您的超越之处在哪里?
高建平:在书中,我用音乐、舞蹈、围棋,甚至以排兵布阵去打仗来谈论中国的画,这些都只是打比方,是以此来说明对绘画的理解。我在书中的本意,并不是说这些活动与绘画相通,而是以此来说明绘画时间的含义。例如,绘画与音乐和舞蹈表演,我是说绘画在时间上具有音乐和舞蹈表演中的性质,但不是表演。这在前面讲过。围棋与绘画的关系也是如此。围棋具有对抗性,讲求取势,从布局到收官的阶段性,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对次序、虚实、死活的理解,如此等等,从这里可以悟出并说明绘画的道理。而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空间的时间化性质。关于排兵布阵去打仗,这在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过,道理与弈棋类似。
谈到宗白华先生,当然,他是现代中国美学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我从宗先生的论著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但我的这本书有几个地方与宗先生显然不一样。第一,宗白华讲中西空间观念的比较,而我主要讲空间中的时间,即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中所蕴含的时间观点,或者如前所说,中国人是如何将空间时间化的。第二,宗白华讲中国艺术是表现性的艺术,西方的艺术是再现性的艺术。我则重点论述一种表现性的动作,讲动作如何沟通主客观,从而论证主客间的统一性。第三,西方非常注重视觉,有着视听领先的传统。与此相似,宗白华也很重视视觉,既然讲的是绘画,不讲视觉不行。而我所要论证的是处于视觉背后、使视觉成为可能的人的感性活动。人在实践的过程中,先有身体与世界的接触,形成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在此以后,才有感性直观。人在感性活动中发展出了感性直观的能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从逻辑上,应该是“实践”领先,然后才有“认识”,而不是相反。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专门论证,这里只能是简单提一提。还是说宗白华先生,我们对于像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学术前辈的观点,不能永远是“照着说”,而是要“接着说”,说出新意来。
Q
安静:在中国艺术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有一种等级化的体系,像黑格尔所总结的那样,诗歌是艺术中最高级的一种形式?
高建平:所谓的等级化,有时候是由于外在的社会原因,并不是内在的美学原因。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文学都是领先的。从政治的地位上来说,从事文学的,常常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处在社会上层。在古代社会里,这些人的地位要高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
西方古代是如此。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剧作家有着很重要的位置,而雕塑家和画家都是工匠。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文人和诗人地位高,而画家是画工,音乐家是乐工。我们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认为“三杰”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其实真正在当时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三杰”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三位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然,不同时期的情况不一样。阿尔贝蒂和达•芬奇认为,视觉艺术地位很高,到了浪漫主义时代,音乐以其抽象性占据特殊位置。我们从事美学研究时,应该具体地说在某些社会,在某些时段,某些艺术常常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影响,而不要泛泛地说哪一门艺术永远具有最高等级的地位。
三、符号学视野:书画理论与20世纪美学
Q
安静:在2023年符号学国际大会的开幕式致辞中,您谦虚地表示自己对符号学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但在《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中,您把中国的文字视为符号,而且认为书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字的符号内涵,中国书画的最终形成是艺术家在特定时间、地点、身体、动作和心理状态的符号。您用大量的中国画论原理论证了中国书画的符号化过程。我认为您的这部著作毫无疑问可以看成是沟通符号学原理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资源的一个经典例示,能否请您谈谈在写作这部著作时所接触到的符号学的思想和文献,这是否和乌普萨拉大学当时的符号学语境有关?还是您之前研习符号学的一种积累?
高建平:我写这本书所接受的符号学影响应该说主要有三本书。第一本是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现在把它译成《感受与形式》。朗格认为,艺术是一种情感的符号,是内在和外在相互对应的异质同构关系。第二本书是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他讲到“制作与匹配”(making and matching)的视觉模式,意思是图像制作本身原本是符号制作过程。这种符号是图式化的,符号实现了对象间的区分,从而成为对象的标志。例如,国际象棋的棋子并不要求与所代表的对象相似。“王”不需要用一个真正的王的形象来代表,而只需要一个王冠的图案。“马”不必像一匹真正的马,而只需要一个马头的图案。“车”也不必像一辆真正的战车,“兵”更不必像一个真正的士兵。棋子所需要的,不是逼真,而是区分,“王”不像“车”,“马”不像“兵”,只要相互区别明显,这副棋就可使用。这时,棋子所起的就是符号作用。绘画原本所追求的也是如此。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由于特定的原因,画家们超越了符号所带来的这种区别性的最低追求,而实现了逼真。第三本书是诺曼•布列逊的《视觉与绘画》,他对贡布里希的观点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在逼真的再现之上,绘画还可以有画家的姿态和动作的体现。此外,还有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他把经验看成了是“做与受”(doing and undergoing)的结合。
当然,在瑞典读书时,也读一些分析美学的书。但是,我的思想一直跟我的那些做分析美学的同学有点格格不入,这也是我后来很喜欢参加国际美学学会的原因。国际美学学会1995年年会的主题是自然美学,1998年讲超越分析美学,2001年讲东方美学。像阿列西•艾尔雅维茨、阿诺德•伯林特对分析美学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我的导师约然•索尔本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希腊的摹仿论研究。他是一位很宽容的人,我反对分析美学的倾向也得到了我的老师支持。我对符号学的探索也是从中国艺术这个角度来做的。当然,我从来没有试图自创一个体系,并将之强加到中国的艺术理论上去。正好相反,我认为,这种体系原来就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书画理论之中,我只是将它呈现出来而已。
Q
安静:随着您的讲述,也让我们看到了您所经历和感受的20世纪西方美学,这一点很有意思。谈到20世纪的西方美学,我们会想到语言学转向、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形式论,等等。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展开谈谈您所感受到的20世纪西方美学?它与您在中国读书的感受存在哪些观念上的不同与联系?您在《中国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后记中,谈起自己当年在瑞典读书,读贡布里希、布列逊、塔塔凯维奇等人的书,对您的思想具有解放的意义,您能谈一下这种解放的最初起点是在哪里吗?在《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的后记里,您写道:“现在感觉到当年读书所形成的这套观念体系,仍有价值,还愿继续坚持。”可否请您概述一下这套观念体系的主要内容,以及您所说的愿意坚持的价值的具体内涵?
高建平:我现在看在瑞典待的八年,当然非常值得。在去瑞典之前,我在中国读的书还是当时的美学四大派,这几大派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到了80年代,大家还在谈。到了8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开始转向中国古代美学。那时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史”的观念的梳理。但是,怎样用一些新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当时还没做到。一些国外的书我们后来很熟悉了,但当时也只是零星地接触,觉得很开眼界。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是在国内读完硕士才到国外去的,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家读硕士,甚至读本科时读的书我都没读过。那怎么办?只有从头读。至于说读的书包括哪些内容,首先是读了一批分析美学的书,另外还读了一些美学史和艺术学理论的书。当然,我在那里并不仅仅是读书,也积极参加系里的seminar。这种seminar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系里的老师和博士生提交论文初稿,供大家讨论。在这八年的过程中,我几乎每学期都会提交一篇文章供大家讨论,其他老师提交的论文讨论我也参加。这种讨论收获很大,能发现自己论文写作中的不足,讨论后再继续修改。系里也经常有一些学者来做讲座,包括后来我们熟悉的一些学者,例如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理查德•舒斯特曼,等等,都去讲过,那时他们还是非常年轻的学者。记得去讲的还有英国分析美学家彼得•拉马克,前不久刚去世的一位印度学者苏克拉,曾去做过系列讲座。
你说到的《中国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这本书,里面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例如讲“书画同源”,讲“描写之辨”,都是这本《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所论述到的问题的展开。这方面的工作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毕竟,这本书当时是在国外写的,资料不足,理论上也还不够完整。希望将来这些理论能得到更好的展开。
△高建平著 《中国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
四、打通古今中西:走向美学之途
Q
安静:原来您愿意坚持的理论体系还有如此宏大的内涵,非常期待您新一步的研究成果。在《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一书中,您大量比照中西艺术哲学的不同之处,我一边读,一边对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很是神往;但同时也有一个感慨,我们现在学者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用电脑写作,对空间的感知方式、对时间的感知方式也由于现在的技术手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书与画也成为一种专业或者是学科,学者们已经不再用毛笔写字了。而古人的画论书论,只有借现代的理论进行研究才能和我们的学术语境形成对话。您如何看待学术进程中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它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是否失去了某些传统的特质?其实这个问题也与进一步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中国性相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高建平:研究中国古代,不能只想回到古代去,或者只是慨叹现在没有古代的氛围了。我们不可能像李白那样,向老妇人学习把铁棒磨成针,像王羲之那样把整个池水染黑。现代社会中生活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其实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思考,我们从古代的材料中,看到哪些东西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回到古代去。不能说只有古代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所谓回到古代才能建立一种纯正的中国立场,学界有很多人喜欢这么说,但这是错的。我们要建立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的理论与传统相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性,适合我们时代的中国性,适合现代技术生活方式的中国性。我们不能用古人来批评今人,而是要从古人那里吸取营养,认真地研究,根本目的还是为现代的中国服务。
Q
安静: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还有一本著作是《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您在其他很多文章当中也谈到,要打破一种固有的观念——说西方等于现代,中国等于古代,您的这本书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美学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个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存在。我们常说希望打通中西古今。这种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比如您在《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中提到的文献问题,当时写作所参考的英文文献是比较受制约的,需要经过自己再进一步的修订。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现在一直说要建立“三大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应该是第一步的,而且现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进一步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其实是不容易做的。从您博士论文的国外出版,到今天在中国的再版,跨越近30年的历史,关于中西对话,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代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有没有更多的中国的画论、艺术理论、美学翻译到国外?您也组织了很多译丛和学术丛书,您对当前中西学术的对话如何评价?
高建平:学术就是要在对话中发展。中华美学学会第一任会长是朱光潜,他那时已经很高龄了,因此一般也就不参加会议,但是每次会议朱先生会给会议发封贺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在贺信中说两条:第一条是不通一艺莫谈艺,就是说美学的理论要和实践结合,没有深刻的艺术感受没法做好美学研究,他自己对诗歌就有很好的研究;第二条是说,青年趁年轻要学好外文,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在交流对话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我们会发现,一批我们以为是研究中国美学、中国哲学的大师们,实际上对于国外都有很深的了解,比方说宗白华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他还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对西方的东西是很了解的。读过《宗白华全集》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也是打通中西的。现在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某些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另外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西方,实际上,中西要打通。美学是一个专业,研究者可以专门化,但各专门研究者要为这个专业的建设服务。
提到“三大体系”,你刚才说的话是对的,话语体系的确是第一步,相比于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而言,话语体系更加零散一些,因此相对容易交流。更进一步的是学术体系,这是话语背后的骨架,通过对比一些概念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背后的学术体系上的区别。各个国家学术体系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比如德国人就比较喜欢在一个大框架内进行学术研究,而英国人就不愿意建构这种大框架,他可以在一种自然的叙述中,把他思想的深刻性慢慢叙述出来。学术体系的建立和交流更不容易,动不动把一个大体系拿来比较,在一些会上泛泛而谈,当然可以说明中国人怎么说、西方人怎么说,但那样的做法不具有生产力,写出来的东西没意思。我们要研究西方的某些概念与它在中国有哪些相近或相异之处,中国有哪些概念可以与之进行对话或者比较,扎扎实实进行研究就很好,所以说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成为一个起点。学科体系实际上更多地与教学连在一起。我们所研究的是美学学科,但不要把美学家再分成这些人是专门做中国美学的,那些人是专门做西方美学的。
另外就是翻译。现在中外交流当然已经很频繁了,也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落实到我们美学这个专业上,交流其实还是很艰难的,真正的中国美学的书翻译成英文的还是比较少。国外的汉学家中做美学研究的也不多,这是个现实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的还是要多交流,多开些会,让更多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来关注美学。汉学本身很难说是一个专业。汉学家也不一定懂美学、会汉语,能译美学书的人很少。对于中国来说,翻译国外学术著作的意义重大。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大量的翻译书,这些书对于中国学者后来的一些思想体系建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些人说外国人思想一来,就把我们思想搞乱了,我绝对不同意!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纯净的中国了?不对!没有交流和对话,中国的美学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很多从事中国美学的人,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通过翻译读了一些西方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激活我们的思想,翻译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当然,我们今天的翻译与以前的翻译会有不同之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况。1980年李泽厚先生说要快快译出来,以应急需;而今天中国加入了多个国际版权协议,好不容易买了版权,我们所需要的是译出精品来,把西方最重要的一些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打造一些汉译精品,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要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做法,跑马圈地,这不行。以后一定要译出一些精品来,不然会遗害无穷。我们今天需要一种安静专心、不焦虑急躁的态度,一本一本地把书译出来,我们需要大批人来做这方面的事情,这样对中国美学的提高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采访人:安静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发布于:北京市新宝策略-配资一流股票配资门户-股票配资学习-配资最新行情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